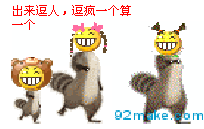|
每听一次大佑的《母亲》,就有一次流泪的感动。
虽然大佑写的不仅仅是狭义的母亲,但我却更愿意在交替的音符和图象中,化为对母亲的感激和怀念。
在此母亲节之际,特以此篇旧文修改,献给天下所有含辛茹苦的母亲们。
叫 早 ——献给每一位伟大的母亲
许多尘封的事情,总是在不经意的外力的触击下,突然泛上心头,一池春水吹皱,那原本平淡的近乎无味的琐屑,竟会闪烁出璀璨的光,而五彩光芒的映射下,往往是一颗苍白而悔恨的心。
一日乘车,半路汹涌的“杀上”一群十二、三岁的女中学生,立时车厢这原本平静的港湾,宛如海啸来临,亦如百鸟归巢,恍惚置身在自由市场的讨卖声中,其中更有一音色秀美的妙龄少女咬牙切齿,一口一个“他妈的”规划着如何将邻班不买她帐的同学“整死”的宏伟蓝图。半车人皆骇然(另半车人是她的同学,早已熟听无闻了),想妇女解放运动至此,却已令人不寒而栗,如再西化下去,大概遍街都是秃头红颜了吧。东方女性的善良、勤劳、温顺而刚强的特性就这样随风飘去,我们却只能说上一句“LET IT BE”,然后在梦中的回忆,体味母亲的平凡与伟大。
儿时,在偏远的中国北方生活。北方冬日的早晨极是寒冷,对于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说,这是个永远睡不醒的时间,这个时刻,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抵御得住温暖的被窝的诱惑。但过去上学的时间总是那么超前,早自习、晨练——总是让我披星戴月,在冽冽的寒风中踯躅在崎岖幽静的小路上,孤独、恐惧使我更加厌恶学堂,心中也不断抱怨把我从被窝中唤出的母亲。
既然我不会象“小二郎”那样勤勉地自动上学堂,母亲也就不得不承担起这“早叫”的重任。本来就无法早睡的母亲就又要早起,为了不干扰其他人睡觉,母亲从来不用闹钟,在她的枕边总放着一只手电,母亲每每在小睡片刻后,就拧亮电筒,看看黑漆的夜中寂寞的座钟,琢磨着喊我起床的时间,如此这样反反复复,母亲总是无法安心入睡,也许只有我走之后,母亲才能小憩片刻,然后便又投入一日的劳碌。而我对于母亲的惴惴和一片苦心,却没有丝毫的理解。一日,劳顿的母亲终未能按点喊我,在母亲惊慌的自责声中,我从温暖的梦中睁开惺忪的睡眼,已经晚了一刻钟,这就意味着我将战战兢兢地去敲教室的门,然后在全体同学的注视下被罚站,甚至还要受到老师铺天盖地的呵斥。对于从未有过此种经历而又一向被老师推崇为品学兼优榜样的我,这简直无法想象。于是,我勃然大怒,冲着母亲狠狠地发了一通脾气,并摔摔打打着脸盆、毛巾、书包,母亲则惶恐的跟在我身旁,口中絮絮着:“怎么睡着了,唉!怎么睡着了”。当我最终拒绝母亲准备好的早饭,摔门而去时,母亲呆呆地立在门旁,眼中噙满了痛苦和自责。我的心终于也有了稍许的不安,但转瞬便在滚滚红尘中湮灭了。
转眼已弃家二十余年,一个人在陌生的世界中东征西杀,满面灰尘,满心疲惫,便越发思念家的温馨,孤寂的夜中,每每被刺耳的闹铃惊起,恍惚之中更渴求能得到母亲的一次“叫早”。但现实总将梦击得粉碎,生活的压力事业的冲击,使我不得不付出家的渴求。不但无法回到家乡,甚至连寄回片言微语都得不到空闲,或者是懒吧。而母亲却不时托人捎些杂物,以致我不得不耽误时间去取,还要搭上许多的人情,心中就生出许多厌烦。于是便带口信回去,希望母亲不要再捎东西,但母亲一如既往,只是次数少了,分量重了。我本想亲口告诉母亲,但母亲噙满了痛苦和自责的眼睛总在暗中浮动,我的心也一次次刺痛,忏悔之中,我终于打消了这个念头。但这忏悔却无法打消,也许将伴我终身,漫漫人生路去独自体味。
孟郊有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但我纵有此心,又何时能够报得春晖,何况,母亲的付出又岂是子女能够回报的呢?“母亲的怀中有个蓝蓝的海洋 曾经你也有一个青春的脸庞 你如此端详的这张迷惑的脸 和那历经风雨和冰霜寂寞的眼 寒冷的冬天依然有夜深寒凉 春天的温暖只因你年幼的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