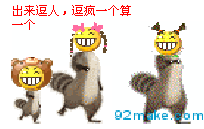|
人类文明的进程,或者大工业化的进程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是幸福还是毁灭?
歌中没有答复,也没有更深度去挖掘这个命题。我相信对此,作者也不满意。不久,罗大佑通过那首石破天惊的《鹿港小镇》将这个探讨更深的延续了下去。
鹿港小镇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 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 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 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 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
想当年我离家时她已十八 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鹿港的街道 鹿港的渔村 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鹿港的清晨 鹿港的黄昏 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
假如你先生回到鹿港小镇 请问你是否告诉我的爹娘 台北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 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
在梦里我再度回到鹿港小镇 庙里膜拜的人们依然虔诚 岁月掩不住爹娘淳朴的笑容 梦中的姑娘依然长发盈空
再度我唱起这首歌 我的歌中可有风雨声 归不到的家园 鹿港的小镇 当年离家的年轻人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繁荣的都市 过渡的小镇 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 哦--
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的水泥墙
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
门上的一块斑驳的木板刻着这么几句话 子子孙孙永宝用 世世代代传香火
啊--鹿港的小镇
在这首歌中,罗大佑放弃了《一样的月光》中通过对环境描写来烘托人性的比、兴手法,而直接以一个“北漂”(漂在台北)自言自语式的感受、回忆和描述,直截了当的述说了大时代下人性的迷失和失去“根”的痛苦。对于听者,这种冲击比《一样的月光》来的更猛更烈。
有人说,《鹿港小镇》写得是青年人理想的幻灭,但不仅如此。六十年代的台湾,正如八十年代的大陆,经济开始逐步腾飞,西方文明潮水般涌进,传统的、沉疴于中国人心中的东方文化开始变异、沉落直至消逝,就连“春风难绿”的古老的小镇也“挖走了红砖砌上了水泥墙”。古老的东方文明已临近了幻灭的边缘,霓虹灯湮没的妈祖庙、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永远烧不净的垃圾和塞车永远塞不停的街道、价格每一天高味道反而不好的苹果、带着面具终日无法面对自己的人类……“异化”终于登陆这块古老的土地。撕天裂地的电吉他中爆发出的“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的呐喊声里,我们听出的更是对古老文明失落的一种感慨。
整首歌充满了东西文化的抗争和排斥,以及失去了自有文明的东方人类的彷徨和无奈,在“台北不是我的家”的歌声中,我们该去寻找一个怎样的家园呢?罗大佑没有回答,也许,没有人能够知道答案。他只能继续用一首首歌曲描绘和记载这个变革的时代:在《亚细亚的孤儿》的唢呐声中我们听到了“在风中哭泣”的中国人的任人欺凌的过去,在《现象七十二变》中看到了蜕变的现在,在《未来的主人翁》中看到了危机的未来,还有《之乎者也》中清贫的教育、麻木的青年、《盲聋》中冷漠的人群。失去了精神家园的人们,从这些歌中找到了共鸣,“台北不是我的家”弥遍了大街小巷。罗大佑以其歌曲中的抗议、抨击和讽刺而被认为是“叛逆青年”,并被带上了“青年时代的先知兼代言人”的帽子。但这并不是罗大佑的初衷,在玩世不恭的表象下面,在轻快的音乐节奏中,在深深的失落和困惑中,你可以看到他对五千年文明的诚挚之爱和对中国人未来命运的忧虑。
这是时代转型时的阵痛,而只有处于这种转型时代的人群,才能够感受这种彷徨而又无奈的无家的感觉。当经济大潮轰然将旧有价值观彻底冲走,当物质财富成为衡量人生和社会的唯一标准时,这种痛苦也就在麻木中消失了。
于是苏芮放弃了“一样的月光”开始了“跟着感觉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愤怒的气力,我们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我,纵然“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只怕“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的幻境,只能梦中去寻找了。
但是时代转型的滚滚潮流居然被天遣的病毒拦腰截断,在这个恍如末世的年代,突然想起了这几首古老的歌曲。“该去的会去,该来的会来,命运不能更改” ,只是在各种病毒的连番洗礼下,我们到底会迎来什么样的未来?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在未来,还有谁会记得这些古老的歌曲?
|